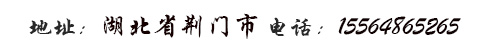唐月近期诗歌读札小辑
|
?唐月,一个惯于为沉默分行的人,诗作见《诗刊》《星星》等。曾获《鹿鸣》年度诗歌奖、许淇文学奖等,现居内蒙包头。? 美莫美兮“落花乱” ——诗人周所同《落花乱》读札文/唐月 一首诗自身的量级决定了人们阅读它的方式,或一扫而过,或品咂再三……而眼前这首《落花乱》显然颇具抓人眼球于瞬间的“杀伤力”,它不容你做出更多的选择,跳读即已条件反射式的完成:“拒绝”、“深渊”、“下坠”、“危险”、“尖刺”、“凋零”、“暴力”,乃至“摧毁一切”,落红般令人惊艳的词语,带着它们超乎寻常的力度与速度,纷纷坠落,且掷地有声,“乱”我们的眸,“迷离”我们的心。 回看,这一堂“暴力美学”课实则由“非暴力不合作”的“拒绝”拉开序幕,“拒绝”一贯的“答应”姿态,在面对“喜欢或爱”时,好诗不走寻常路,因为好诗人不答应,好的“喜欢或爱”也不答应。随后,诗人便开始触摸“万物”的“深渊”,并在它们“下坠”的过程中,应许它们由此而“看见危险的云彩”,由“深渊”及“云彩”,如此大幅度的想象力的蹦极,确实在考验我们坐诗意过山车的能力之余,也令人不得不叹服诗人对一首弹性十足的诗游刃有余的掌控力与激荡其间的无限活力。 “知道的愈多相信的愈少”,话说的自然也“愈少”,“智者从不雄辩”,嗯,卡莱尔有言:“雄辩是银,沉默是金。”而让“沉默”以“沉默”的方式言说,并被诗歌不经意间捕捉了去,无疑就是钻石了。于是,作为“智者”的诗人,应允作为“智者”的“草木”“一边”静静“匍匐”在地,“一边”默默“生出尖刺”,准许“落花”在静静“凋零”之余,默默以其“美和暴力”“迷离”这个人世间,并终以诗歌的名义给予它们“摧毁一切”的神秘力量。这“顺从”背后的不“顺从”,隐忍背后的蓄力,忽地令人心生敬畏与悲悯,读来不免心疼。 同样写“落花”,诗人周所同笔下之“落花”全无欧阳修“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绝望和感伤,也丝毫不见晏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与惆怅,他意不在作黛玉们自怜自哀的“葬花吟”,也无心进行龚自珍式“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庄严宣誓,也即周诗显然在“拒绝”继续于传统诗学范畴内“落花”这一意象业已固化的意义上徘徊不前,而旨在特写“落花”“赴死”之“决心”、之绝色、之决绝,个中孤绝、悲壮之美与诗人代薇笔下的同名诗《落花乱》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漫天飞舞的花瓣像赴死的快心。/一场浩大的叛乱/英雄必须冤屈,美人必须夭折/而时间,必须浪费”。二者读来,都让人由不得想到霸王别姬那一场美殉英雄戏。嗯,悲莫悲兮王别姬,美莫美兮“落花乱”。 .3.11 附诗:落花乱 文/周所同 喜欢或爱,先从拒绝开始 万物皆有自己的深渊 敢于下坠,才看见危险的云彩 知道的愈多相信的愈少 智者从不雄辩,比如顺从的草木 一边匍匐一边生出尖刺 落花不是凋零,是迷离 的美和暴力,可以摧毁一切 ?雨中“听雨”,也听你 ——诗人潘京《听雨》读札 文/?唐月 无独有偶,我的天空不知是否缘于领受了你《听雨》诗的神启,一早便淅淅沥沥地开始落雨。不同的是,作为一个惯于眼馋的视觉动物,我过早地移步窗前,忍不住饱眼福去了,而你却依然在纸上“听雨”。“它是铁的,不怕雨。/它是白色的,不必洗刷。”耳中之雨,与金属碰撞出了金属之声,“铁的”“它”不怕淋湿,竟也无惧锈蚀,洒脱之至;耳中之物,亦自有其颜色——“不必洗刷”的“白色“,欲拒还迎,欲迎还拒的“个色”(注:在此不含贬义)。“听雨”听出了万物的个性,非有个性之诗人所不能为也。听什么都是在听自己,什么听都是自己在听。“它是我的马,就要跑起来了。“仿佛一个更为神圣的天性渗透到我们自身的天性中,只是它的脚步好似一阵掠过海面的风”,雪莱在其《诗辩》中曾这样来描绘令造化加速,让神灵放慢的“缪斯的到来”。在此,缪斯附身的诗人天马行空,呼风唤雨,只身打马过原野了:“绿色的田野就在它的身后,/把它催促,把它追赶。”一动俱动,画面随之奔腾起来,速度与力度惊人,充满了不羁的野性之美。而这美,无疑因了诗人充满活力的个性之美。“那是一条河,它不怕雨。/它的水是透明的,不怕一滴雨的来访。”“不怕雨”的显然都在雨中得到了净化与救赎。“透明”之物彼此间天然有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谁遇到谁,都是朝向彼此的皈依。两个“不怕”中,诗人听出了灵犀,雨,一点即通。川纳百雨,一如海纳百川。诗歌有容乃大,诗人有容乃大:“我是一个听雨的人。/我不怕雨落在任何地方。”当诗人又一次重申“不怕”的时候,一个从容淡定的“听雨人”的形象已跃然纸上:她既非“夜来风雨声”中挂怀于“花落知多少”的“听雨”诗人孟浩然,也非“僧庐下”,“鬓已星星”,深知“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的“听雨”诗人蒋捷,更非“且听萧萧暮雨声”“老态龙锺疾未平”的“听雨”诗人陆游,诗人潘京在雨中“听”出的并非死亡的讯息,而是生命的福音:“我听见一粒隐匿于黑暗的种子。/雨水过后,它就要开口,/田野已经张开眼睛——”似曾相识燕归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与老杜一样,在其诗中,潘诗人也是“喜雨”之人;在她耳中,雨也是“喜雨”——“知时节”的“好雨”,它正将“隐匿于黑暗的种子”带往光明的去处,它将打开它们被封的口,“张开”“田野”被蒙的“眼睛”,让该说的都说出,该看的都看到——一切关于雨的美意与春的真理。“它是一首歌,就要唱起来了。/春风把它吹拂,/把它催促,把它追赶。”面对扑面而来的春风,无需辨认与区分,诗中所有的“它”都是一个“它”——沁人心脾的春雨,都是一个你——听雨者,与“雨”共舞的“雨”,和听“听雨”者同频共振的雨一般的“透明”灵魂。 .3.18附诗:听雨文/潘京它是铁的,不怕雨。它是白色的,不必洗刷。它是我的马,就要跑起来了。绿色的田野就在它的身后,把它催促,把它追赶。那是一条河,它不怕雨。它的水是透明的,不怕一滴雨的来访。它是一首歌,就要唱起来了。春风把它吹拂,把它催促,把它追赶。我是一个听雨的人。我不怕雨落在任何地方。我听见一粒隐匿于黑暗的种子。雨水过后,它就要开口,田野已经张开眼睛—— ?“雪”、“月”可诗,道亦可诗 ——诗人徐南鹏《雪》读札 文/唐月 记得初读这首诗时,我竟误以为末句“一些”是“一切”的笔误,当诗人南鹏说道:“一些,是不是好一些?”时,我才反应过来:哦,“小些”、“慢些”、“难些”、“易些”、“一些”,全诗六句末有五句都无一例外地用了“些”,这显然不是有意为之的前呼后应,而是南诗一贯的风格:下笔轻。一如猫行雪上,所到之处,无非只留淡淡的印痕,它无需每走一步都掘地三尺。 一首诗用力太猛,极易拉伤自己,将自己打翻在原地。深谙语义平衡术的人,更懂得如何在不动声色的轻描淡写中做到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文如其人,一个言行极有分寸感的人,笔下很少出现极其浮夸的诗句,他们一般慎用夸张手法,因为那样反显得太过轻佻与轻飘。 “雪”诗在对比中逐句展开:先是“城里的雪”与“城外的雪”的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下得小些”,一个“化得慢些”。一“城”之隔,天壤之别。这“雪”下得意味深长。虽然诗人只是冷静地叙述,但个中缘由耐人寻味:究竟是什么缩水了、逼退了一场大“雪”呢?“城”当扪心自问了。好诗往往点到为止,欲言又止,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轻轻地说,淡淡地说;大说特说,把话说尽了,说透了,诗就没了。留白的部分,往往才是诗之所在,所谓诗言有尽而诗意无穷。 接下来是两个“改变”的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改变外部环境难些”,“改变内心感受易些”。嗯,佛家讲:万法唯心造。心有一切有,心空一切空;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较之向外求变,求诸己心之变无疑更为明智与通达。而以上这两个“改变”显然是在为最后的一个“真正改变的”做铺垫,“唯有月”三个字在此推出,水到渠成,且特别打眼。“它以阴晴圆缺告诉我一些”。月亮是位现身说法的好老师,它借东坡之口在教给我们“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沧桑正道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千里共婵娟”的机缘与夙愿。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雪”、“月”是“天”,“小”(包括与之相对的“大”)、“慢”(以及隐含其后的“快”)、“难”、“易”及“阴晴圆缺”都是“道”,而“它以阴晴圆缺告诉我一些”,即是“道法自然”,人法道。诗人以其短短六行小诗,巧妙地诠释了“道可道,非常道”,而其对至简大道和“雪”与“月”的钟爱也由此可见一斑。嗯,“雪”、“月”可诗,道亦可诗,此诗可圈可点。 .3.23 附诗:雪 文/徐南鹏城里的雪下得比城外的小些 城外的雪化得比城里的慢些 改变外部环境难些 改变内心感受易些 真正改变的,唯有月 它以阴晴圆缺告诉我一些 ?于“锁孔”间聆听“落在水里的雁鸣”——诗人李东仁诗歌读札 文/唐月 此前,不熟悉诗人李东仁的文字。昨晚集中拜读了其二十多首诗,粗略印象如下:这是一大组颇具古诗词典雅气质但又不乏现代意识的新诗,而且越往后读,感觉现代性越强,那些基于作者深厚古诗文造诣而易落的窠臼逐一被打破,诸如“柴门”、“苍苔”、“陌上花开”、“一湖平水”等古诗词中常见的意象与意境越来越少出现,继而代之以更为贴近生活、接通地气的事物的不断呈现及颇为现代性、陌生化的生动表达,因而呈现出一种古风之美与新诗气息兼具的喜人丰姿。 听听“落在水里的雁鸣”,视听上湿漉漉、水灵灵的感觉扑面而来。随后,这雁鸣声声“划过长空,划过厚土”,于水天之间,天壤之间,起起落落。画面弹性十足,诗意游刃有余。于秋高气爽、风轻云淡的开阔之境中,“芦花”“次第”“白”过来了。“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季节的中老年色彩蓦地在一幅动图中铺排开来,令人猝不及防:“恍若我鬓边的呼唤”,不用说,这“呼唤”也是白色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此处最妙的还不仅仅是诗人信手拈来的通感,或说移觉,而是由此进一步点燃的灵感、灵光,及随之掷地有声、令人耳目一新的神来之笔:“奇迹般寻得我”。小诗到此戛然而止,而无穷余味已弥漫开来…… 不妨再端详一下我们司空见惯、视而不见的“锁孔”,“像盛满昔日瘦长记忆的巷口”,一个新颖的比喻,一下子将时空拉长到“昔日”之“巷”。“记忆”以“瘦长”言之,既紧扣“锁孔”的特征,又暗合了“巷”之奥义,同时也人格化了它们,使得原本冷硬的“锁孔”顿时得以升温和软化,熨帖了任何一位读到它的游子的心。“沿着裂缝里时光倒流/那样柔软的故乡,还要等多久/让我能转动指间的/沧桑”,“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一首《长歌行》吟旧了“东逝水”,而东坡却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一如兰溪溪水尚可西流,诗人亦能“沿着裂缝里时光倒流”,只是,他尚需“等”,只待“柔软的故乡”应许他“转动指间的/沧桑”。读到此处,“柔软”一词以其极富女性特质、母性特质的阴柔之美再次软化了我们的心,将其与“故乡”二字拈连,不禁令人叹服诗人以此陌生化手段处理定中关系背后的敏感与细腻,匠心与真意。 《落在水里的雁鸣》与《锁孔》,均为五行短制,但诗人以其简约却极具包容性的文字于个中所隐现的岁月沧桑与时空变迁的母题却阔大得多、深远得多,运笔可谓惜墨如金,四两拨千斤。于“锁孔”间聆听“落在水里的雁鸣”,我们隐约听得了诗人打开其诗歌季的钥匙的天籁之音。 .4.4 附诗:落在水里的雁鸣(外一首) /李东仁 落在水里的雁鸣 划过长空,划过厚土 芦花便次第白了 恍若我鬓边的呼唤 奇迹般寻得我 锁孔 /李东仁 像盛满昔日瘦长记忆的巷口 沿着裂缝里时光倒流 那样柔软的故乡,还要等多久 让我能转动指间的 沧桑 ?诗人“长恨”诗不“恨”,“恨”到“长恨”诗愈工——诗人大解《长恨歌》读札 文/唐月 峰峦如聚,聚的是“沉默”。此处或有“如怒”“波涛”,但犹在水面以下,诗意在风平浪静的“沉默”中不动声色地铺开。“沉默的群山在北方聚首”,“北方”适合千年的“沉默”,适合再“沉默”千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条曾“未选择的路”带着我“迟到了”。“我”是另一个沉默——令沉默成为沉默的沉默,一如海德格尔“让存在者成为存在者的那个存在”。“时间通过我而拐弯”,“我”是另一个时间,令“时间”拐弯的时间;“引开了散去的人群”,“我”是另一个人群,令“人群”散去的人群。以一当十者,不怕孤独,就怕不孤独。“我请过假,但没有获得批准,还是来了,/迟到了”,一个自由的灵魂通常不会被“准假”,但它不会因之而失去自由。心灵的长“假”不会轻易遗失。即便“迟到”,也会到,不会永远缺席。“可是,/凉风为何如此急迫,不原谅我奔波的一生?”,“急迫”的永远是“凉风”,“不原谅”的永远是“急迫”者,一如“迟到”的始终是“我”,不急于解释的始终是这“一生“的“奔波”。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氏“大林寺桃花”是个绕不过去的答案,一如“北方”“沉默的群山”绕不过“我”。“长恨”吗?如若“长恨”,也只能是“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刘二十八早说过了。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较之白居易“长恨”红颜误君,爱情误国的《长恨歌》,走出弄堂,走进爱丽丝公寓,美人王琦瑶走进美梦,便再也走不出噩梦,较之王安忆“长恨”红颜误己,爱情弄人的《长恨歌》,诗人大解貌似属于一己之憾的“长恨”,实则正是所有不被这个世界的“凉风”接纳和“原谅”的所有瑟瑟发抖的“迟到”者、“沉默”者为“沉默”而“沉默”,为“长恨”而“歌”的共同心声,诗人只是在这里默默为沉默分了个行。固然,“迟到”误人,“沉默”误人,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迟到”与“沉默”也成全了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嗯,诗人“长恨”诗不恨,“恨”到“长恨”诗愈工。 .4.13 附诗:长恨歌 文/大解沉默的群山在北方聚首。我迟到了。 时间通过我而拐弯,引开了散去的人群。 我请过假,但没有获得批准,还是来了, 迟到了。可是, 凉风为何如此急迫,不原谅我奔波的一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imenghuaa.com/mmhgx/10112.html
- 上一篇文章: 每日一味中药牡丹皮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